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
“生命政治”是近几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受到许多学者的追捧。然而,说到生命政治,我们不得不提起这么一个人——那就是福柯。生命政治这一概念虽然并非福柯首创,但它在福柯那里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成为了一种政治哲学——既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哲学,也有别于20世纪其他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
本次讲座我们有幸请到了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的于奇智教授,他将带领我们走进福柯的哲学世界,与我们一起探讨、剖析福柯学的生命政治向度。于教授以此讲座向他的博士生导师韦尔纳教授表示敬意!
事不宜迟,小编即刻为大家送上干货满满的讲座内容!
![3LJI76TLBF]NZU_8B`O)[NF.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0283747720.png)
代表作:
福柯本人所著的书不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下这几本:《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2018)。
领域:
福柯主要运用法国理论和法国历史认识论这两大理论,去研究心理学、精神病学、性欲、监狱、政治、文学等领域的内容。
福柯概念:
福柯概念包含档案、生命政治、生命权力、装置、陈述、知识图式、治理术、异托邦、惩戒机构(制度)、可见性……虽然这些概念不都是福柯所创造的,但福柯对它们进行了转化和发展,因此成了福柯概念。
而今晚,于教授的讲座主要聚焦“生命政治”这一概念。
![_K)Z4X92G$]4JG3_K1FYNH0.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0803510744.png)
在上述内容中,于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关于福柯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现在于教授将正式带我们走进今天的主题——生命政治。
以人口—生命为对象,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治理,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生命政治,是福柯在70年代中期的重要主题。
但“生命政治”一词其实很早就诞生了。早在1851年,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提出社会权力和生命权力,就可以从中窥察出生命政治的影子。随后在1905年,瑞典政治学家契伦在其所著的《大权力》中就提到了生命政治;在1938年,罗伯茨写了一本名为《生命政治》的书。渐渐地,“生命政治”在欧洲得到广泛使用,成为书名、刊名、学会名或书刊阐述的主题。

目前,福柯阵营与国际政治学学会阵营是“生命政治”生成的影响最大的两个阵营。在福柯阵营中,“生命政治”表明权力行使的基础由领土转向个体生命与人口生命(即领土政治转向生命政治或人口政治),由此而生成的权力便是生命权力,它重在探讨生命的社会政治权力。福柯学的生命政治是哲学向度,导向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的区分。而在国际政治学学会阵营的语境中,“生命政治”(最好译作“生物权力”),表达了生物学与政治学的密切关系,它是生物政治的政治学向度,导向自然主义与政治主义的区分。以上两大向度之间虽然存在断裂分岔,但它们也可能走向交叉重叠,有会通融合的可能性条件。
这部分内容并不容易理解,大家是不是有些费解呢?没关系!在下文“ 福柯生命政治的位置”中,于教授会更细致深入地剖析“生命政治”这一概念,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学习。

于教授认为,福柯学主要有四个维度:知识、权力、伦理与审美,主体概念贯穿其间。而“生命政治”这个被评论最多、颇具生产力的概念,无疑属于权力维度,并与生命权力、治理术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崭新的三核概念。此外,福柯的生命政治关注现实的东西。简而言之,生命政治不仅关注个人及其生命,还关注健康、寿命、卫生、出生率……它以哲学姿态面向人类实际问题。
![%N1%%4J07E2}W]1{8N[2@D9.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1369791010.png)
17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国家理由是确保生活和人口的质量,国家理由的治理艺术是优化人口,改善生活,促进幸福。但国家理由在18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开始了。自由主义倡导的简朴治理同包揽一切的国家理由不同,它要求尽可能少的治理,并确保生活的安全。这使得它看上去像是同国家理由的决裂。在福柯在《自由主义治理艺术》一书中写道:“自由与安全性的游戏,就位居新治理理性(即自由主义)的核心地位……自由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也就是我称为权力的经济的问题,实际上从内部维系着自由与安全性的互动关系……来确保个体与群体遭遇危机的风险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于教授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自由主义放置在了生命政治的范畴。
在1979“生命政治的诞生”的讲座中,福柯系统地阐述生命政治。他认为,要弄清生命政治的本质,就必须探索其条件与基础,即质疑新自由主义,即必须摆脱对新自由主义的“怀旧情结”。所谓怀旧情结,即我们通常将“新自由主义”看作是一个贬义词,认为它具有否定性、摧毁性与消极性。但福柯认为,我们应质疑和鉴别新自由主义的传统看法,要别样地看待新自由主义,并挖掘新自由主义肯定、积极的一面,建立与以往不一样的思考。从而使人们获得良性的知识,并推动社会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HSL]3NCQ14MCWPYPP44]BYN.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1934864422.png)
生命政治的双重指向是指,生命政治既指向个体又指向群体。生命政治指向个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何又说生命政治也指向群体呢?这看上去似乎就有些难以理解,于教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前面的讲述中,我们知道生命政治关系到生物、躯体、身体、医学。而在18世纪以前,各种疾病(特别是瘟疫)的流行抑制了人口的发展。到了18世纪,由于人类的生存条件改善和疾病、怪病的减少,人口开始了大幅度的增加。在这种条件下,以卢梭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将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家的思想转为一种更有效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学问。简而言之,就是如何把治理家庭成员的家政学提升到国家层面?如何把家政学发展为政治经济学?这为18世纪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解决暴增的人口问题提供了知识上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命政治不仅指向个体,它还指向群体(人口)。
![]]T[@EJW9)GO[[PG1BYLL16.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2738138519.png)
在上述基础上,于教授想和我们进一步探讨“生命政治人”的可能性与构想。
在于教授看来,人口问题在18世纪如此突出,甚至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特色。因此,于教授认为人口在18世纪已然成为全新的“政治人物”,即“政治主体”。福柯指出,我们谈论生命政治,就是用来指出是什么让生命及其机制进入精确领域,从而对人口进行精打细算;其次又是什么把权力/知识变成了人类生活变化主体。也就是说,生命政治把人口引入一个严格的知识体系中,它心系人口,而在于教授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人口政治。
![U][PO0{@PMTF8U@}HO6}22Y.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2822873502.png)
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探讨生命政治就是关于人口(活着的)的总体问题,这要求我们用环视观来看待这一切。何为环视观呢?于教授认为,环视观就是要看到社会的一切,特别要看到社会良性的东西,不管是理论还是现实。环视主义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社会问题,要力图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治理;并且是要那些治理者都在监控之中,而不只是针对被治理者。环视主义是福柯在边沁环视监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边沁所构想的“环视”仅针对监狱,福柯则把“环视监狱”这个模型扩展到学校、工厂等,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环视链条;当环视链条组成一个群岛,则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不仅仅把微观与宏观各自内部的领域联系起来,而且也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个领域联系起来,从而使整个社会实现了国家治理化。这是福柯在边沁环视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福柯的政治哲学思想摆脱了“宏观国家治理”这一传统思维,它聚焦到了各个具体的、流动的机构上。

此外,福柯认为批判是一种治理艺术。在福柯看来,对于国家的治理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需要一种艺术来调节。在18世纪以前,国家的治理仅仅局限在领土上而忽略领土上的居民和人口。福柯的治理术正是要转变这种传统的治理艺术,要求合理地转向人口治理,做到治理化与细微化。国家的治理由司法转向了行政,国家的职能由统治职能转向治理职能,走向服务型政府这一层面,实行尊重人的治理,这也体现了边沁环视理念的作用。

于教授首先提出权力技术学的双重向度:个体与人口,或者个体惩戒与人口调节。他认为权力技术学指向于个体和人口这两个方向,这也是此前提到的生命政治的双重向度。
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关注自我外,还存在大量的关注他人的现象。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不仅指个体改变自我,而且还指个体在他人的帮助下改变自我——牧师就是这样一个帮助他人、关注他人的代表。牧师权力是具体的、特定的,它针对着个体和个体的灵魂。它与希腊文化发展而成的政治—法律权力相互补充。前者针对着个体,后者针对着全体;前者是拯救性的,后者是压抑性的;前者是伦理和宗教性的,后者是法律和制度性的;前者针对灵魂,后者针对行为。但是在18世纪,它们巧妙地结为一体,形成一个被权力完全控制的国家。因此,要获得解放,就不仅仅要对抗总体性的权力,还要对抗个体化的权力。最终,救赎式的牧师权力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命权力,政治也因此变成了福柯反复讲到的生命政治:政治将人口和生命作为对象,力图让整个人口,让生命和生活获得幸福,力图提高人口的生活和生命质量,力图让社会变得安全。
因此,于教授认为,治理社会不像治理国家那样,追求治理的最大限度化,而是追问治理对于社会的必要性以求其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福柯认为自由主义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就治理实践来说,自由主义起到了调节模式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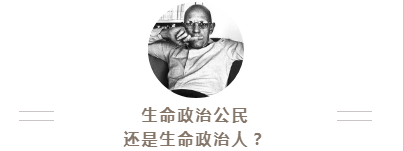
最后,于教授想要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生命政治公民还是生命政治人?
生物公民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化主体,它是一种新的公民权表达,即活人成为生命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活人开始进入生命政治,并与之产生结合,而生成活的生命政治。福柯在研究新自由主义过程中,他特别关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人”这一概念——一个极具生产力和生殖力的概念。经济人作为框架和模型,不仅适用于经济行为的人,而且还适用于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人。于教授想把经济人这个概念推广到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上,即把经济人概念的有效性和应用性延伸到生物公民上。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第欧根尼问题:“你是哪里人?”于教授的导师韦尔纳教授指出:“我是世界公民,真正的公民资格就是延伸到全世界的。”而于教授认为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生命政治。人们可以说自己是生命世界公民,或者说生命世界主义者。生命世界围绕着生物学聚集而成,使用“生命政治”这一术语体现了人类生命问题在政治、权力以及知识领域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因此,生命政治中的公民无疑是一种新公民或新世界主义者。可以说,福柯生命政治及其相关概念把生命政治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让人们看到生命的至上性。因而,我们可以利用人与公民之间的含混性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必去计较他们的分别,并让人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缩短至融为一体的关系,以达到共同感。这也正如于教授所言:“我是生命世界公民,也想是生命政治人,也许正在孕育中。”最后,于教授总结:无论如何,生命政治及其相关项都得面对整体大众及现实问题,这也是生命政治的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

![0(7]1E_ZE0IRID`W}J3(7C4.png](http://statics.scnu.edu.cn/pics/lib/2019/0516/1557974599418398.png)
学生1(男生):老师好!我是来自政治与行政学院的同学。据我所知,自然法思想也有提到生命世界公民这个词。比如在西塞罗的《论法律》、《论共和国》这两本书中,就认为世界公民概念是指全世界的人都基于一种理性的禀赋。那我想知道,老师您本次讲座提到的生命世界公民的概念是从何而来呢?
于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世界公民这个理念最初来自第欧根尼,他想要促成世界主义者。第欧根尼“你是哪里人?”的问题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两次出生:第一次出生来自我们的诞生地;第二次出生则是我们离开诞生地之后去到的远方,这相当于一种摆脱。在这基础上,我想提出生命世界公民的概念,并对它提出一个设想:在对人的确定上,生命世界公民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或定义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动物”。除此之外,我认为人还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存在者,“人是政治动物”这一说法是从侧面对人进行了界定。而在我看来,生命政治无非是在政治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内涵,缩小了外延。因此,我们可以用环视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世界公民,它的概念来源可以追溯到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时代。
学生2(男生):老师好!您在讲座中说“生命政治针对于群体,算是一种治理的手段”。那么我想知道,生命政治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会偏重于哪一个。比如说,国家治理人民,它是偏重于国家还是偏重于人民呢?还有一点,对于主体与客体有什么要求吗?
于教授: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主客二分。其实,主客问题是环视理念的一种体现。在前面我们说到,环视观念就是看到一切,这里所说的“一切”不仅包括主体,也包括客体;不仅有治理者还有被治理者;不仅有臣民还有君主,最后君臣一起构成活生生的人口。而人口是涵盖个体的,并没有排斥个体,因此个体没有消失,这就是生命政治的一个发展和普遍化的推进。因而,我们所有人都在治理与被治理之中,并不存在主客之分。当然,环视主义的这种美好仅仅存在于理念中,在现实中并非如此,但这不妨碍我们对环视主义理论的探讨与模型构造,因为模型的建构总是需要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的,我们应不断去了解社会的进步。最后,我建议这位同学去阅读康德“三分法”,读完之后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同学3(男):我是来自文学院的学生,我最近在写的论文涉及到生命政治的有关内容,因此想在生命政治这方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请问老师您能给我推荐一些书吗?
于教授:我主要推荐你去阅读福柯如下四本书:《必须保卫社会》、《性经验史》、《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我建议大家尽可能读原著,或者英汉法三个版本一起对照阅读,这样会有更大的收获。其次,我认为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的书也值得一读。
同学4(女):老师您好!我想知道在当今时代,我们应怎么理解生命政治?
于教授:所有的词或概念,所有人都可以用。举个例子,希特勒也用生命政治,但生命政治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一种纳粹主义。他主张划分民族的优劣,并为了保卫优等民族的生命而去灭绝其他种族的生命。纳粹主义造成极其惨重的后果,是人类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因此,不同的人对一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要在具体环境中去理解它。这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

读者留言